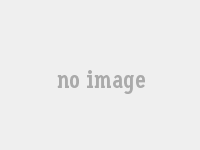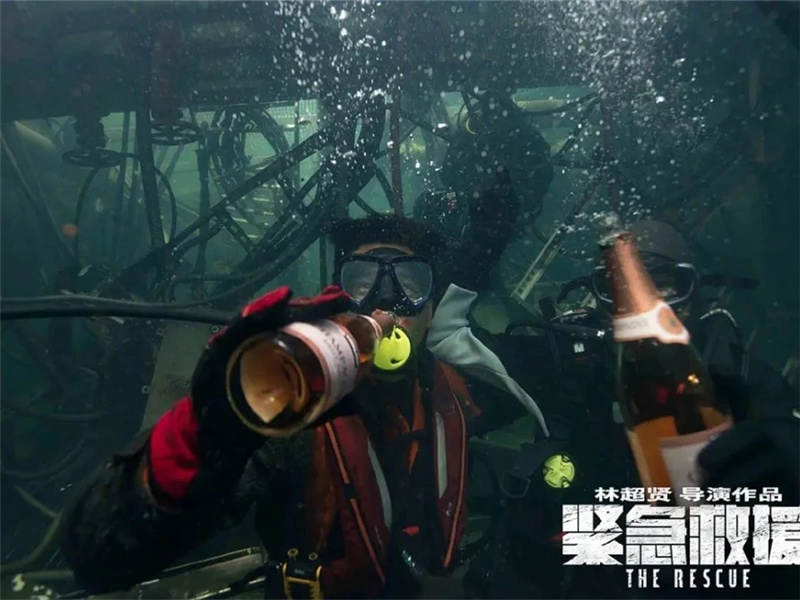两天前,2019年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公布,这个奖项在行内俗称“奥斯卡姐妹花”,Netflix(网飞)出品的《罗马》保持秋冬评奖季一枝独秀的势头,《宠儿》《绿皮书》和《波西米亚狂想曲》分摊了最重要的奖项,这些让一个月后颁奖的奥斯卡奖眉目清晰起来。
其实,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公布的当天,搅动好莱坞工业格局的重磅级产业新闻也公布了:Netflix被美国电影协会接纳成为迪士尼、派拉蒙、索尼、福斯、环球和华纳之外的第七名会员,“网络大电影”的行业地位得到确认。
先前被认为“标准奥斯卡面相”的《登月第一人》《无间炼狱》《领先者》等,在奥斯卡提名中几乎一无所获,Netflix出品的《罗马》和《巴斯特民谣》两部影片则揽下15项提名;《月光男孩》导演巴里·詹金斯的新片《如果比尔街能说话》被排除在主要奖项之外,而《黑豹》经历各种争议和波折后,挤入最佳影片的候选——这是超级英雄电影第一次正式进入奥斯卡评选体系。过去的奥斯卡大户、“大鳄”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官司缠身,新兴的Netflix正式“上位”,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今年奥斯卡评选的影响。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好莱坞产业格局的变化,奥斯卡的话语权正在转移。但是,“变”和“不变”的平衡又很微妙,奥斯卡在肤色、性别和审美的维度更多元了么?答案未必乐观。
“我曾拿过奥斯卡”的导演们,一律被无情忽略
入围最佳影片的八部作品中,翻拍版《一个明星的诞生》最是雷声大、雨点小,自导自演的布莱德利·库珀野心勃勃,可惜被评委无情忽略,他最在乎的“最佳导演”提名落空。
《一个明星的诞生》被排除在核心竞争行列之外,原因是很明显的:库珀在这部经典翻拍中,没有表现出和经典对话的能力,导演层面的想象力和实践能力都是有限的。主演Lady Gaga不能把一个“从尘埃里爆发出巨星光彩”的无名姑娘演得让观众信服,一大半是因为库珀指导演员的能力不行,当女主演力不从心时,包揽了导演和男主演的库珀频繁用“一枝独秀”的特写突出自己,这就非常不讨喜了。
库珀的导演处女作成了最佳影片竞争中的陪跑,更有一群曾和它一起在秋季影展中风光露面的“事先张扬的种子选手”,默默地从今年奥斯卡的小世界经过。达米恩·查泽雷是奥斯卡应试系统里的“好学生”,《爆裂鼓手》一鸣惊人,《爱乐之城》功亏一篑,到了这一部《登月第一人》——把“美国英雄”的题材拍得四平八稳,一目了然是为了修成正果,没想到等赛季正式拉开后,它泯然于众片。关于《登月第一人》的遇冷,猜测与八卦甚多,流言衍化成奥斯卡的密室政治。倒是法国《电影手册》的一篇评论中肯地分析了电影本身的得失:“导演的确是欠火候的,他既想再现英雄的时代、又试图从反英雄的立场反思时代,这份难于安放的表达野心导致影片的失衡和失控。”
《登月第一人》的首映在威尼斯影展,同时期进行的多伦多等影展中,《为奴十二年》导演史蒂夫·麦奎因的新片《寡妇联盟》,《月光男孩》导演巴里·詹金斯的新片《如果比尔街能说话》,《在云端》导演贾森·雷特曼的新片《领先者》,都被认为将造成“奥斯卡大年争锋”的场面,结果这些“我曾拿过奥斯卡”的导演们,今年一律被无视了。
被忽略的还有泽米吉思和伊斯特伍德这些老年人。泽米吉思的《阿甘正传》是很久以前的传奇了,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从巅峰一落千丈,随波逐流,《欢迎来到马文镇》是这位老将尝试重新被主流评价体系认可的作品,改编自同名纪录片,讲述一个战后被心理创伤困扰的老兵怎样在一个用玩具人偶创造的小世界里逃避。很遗憾,《欢迎来到马文镇》只获得了视觉效果行业协会的提名,不足以弥补它的票房失利,并且,它彻底地被奥斯卡忽略,没有获得任何提名。伊斯特伍德也被翻篇了。88岁的他自导自演了《骡子》,扮演一个卷入墨西哥贩毒集团的二战老兵。但这一次,《骡子》没能像《百万美元宝贝》《硫磺岛来信》和《美国狙击手》那样单刀直入地闯入最佳影片的候选行列,它甚至不能像两年前的《萨利机长》那样引发足够的关注和讨论。
商业诉求和美学评估之间南辕北辙
奥斯卡提名名单中明里暗里的“换血”,真相是好莱坞内部的焦虑,作为全世界最强势的娱乐产业,它不得不面对一个迫切的议题:如果好莱坞崇尚的“西方/美国/白人”的优先权旁落,艺术创作和娱乐产品该怎样再现或重新设置一个世界体系?正是这份焦虑,促使奥斯卡评选系统对影片题材和导演人选展开了一次迭代式的洗牌。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八部最佳影片候选中,《黑豹》是“C位”(中心)选手。《黑豹》掀起了足够的风波,为了它,差点增设“最受欢迎流行影片奖”。围绕它能不能入围最佳影片的质疑,能凑一部悬疑片。它抢到“八分之一”的席位,却被排挤在导演、编剧和表演类这些重要奖项之外,活生生上演了一幕职业伦理剧:在好莱坞,卖得好和拍得好各自为政地坚持着两套不兼容的评价体系,而且分歧越来越大,商业诉求和美学评估之间南辕北辙,近似南北战争。
在当下好莱坞的产业格局里,《黑豹》是一部重要的电影,不仅因为它是2018年票房最好的大片。《黑豹》是好莱坞第一次把“超级英雄”的角色交给一个黑人男主角,让他承担“拯救世界,拯救人类”的使命。在此之前,从地理和人文层面完整涉及非洲的好莱坞电影只有《狮子王》,一个人类的非洲王子以主角的身份加入美式超级英雄的阵容,这个转变在电影工业语境中是个大事件。作为一部面对全球市场的商业片,《黑豹》传递了一部大规模娱乐产品的真相——生产者在虚构中想象一个可以接纳的现实,甚至可以说,《黑豹》的立场,极大程度地折射着好莱坞当下的态度。
哲学家齐泽克的评论一针见血:“我们在等待一部像《黑豹》的电影,但《黑豹》不是我们等待的电影。”这电影让人们看到,好莱坞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中议题设置的变化,叙事的初衷是反思“美国优先”的价值观,但作品实际展开的过程中,求新求异的姿态终究归于暧昧,强行转入老派、看似安全的价值观,老调重弹“强者不可独善其身”,当一群黑人在银幕上喊出“瓦坎达万岁”,映射出的依旧是美式价值观的镜像。齐泽克非常犀利地指出,《黑豹》背叛了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的精神遗产:“X意味着在白人的世界观之外构建一套新的体系和新的认同。”
好莱坞没有勇气挑战这种有争议的世界观,恰如美国文艺理论家詹明信总结的,想象一个真正的新世界是艰难的。《黑豹》呈现的是科幻、巫术、未来景观和原始非洲混搭的奇观,是一群非洲人穿着西方的奇装异服进行角色扮演的游戏,被西方异端思想蛊惑的非洲人破坏游戏规则,深受西方正统熏陶的非洲人捍卫秩序——发明这套话术的好莱坞是多么有自我优越感。
我们没法对一部商业大制作的觉悟有过高的要求,可文艺的《绿皮书》也好不到哪里去。《绿皮书》的一对主角,白人司机又穷又糙,黑人钢琴家尊贵得像个法老,看起来是把种族人设的刻板印象给颠倒了,创造了“十分钟笑一次”的惊人笑果。但熟悉好莱坞经典作品的观众会很快联想到,《绿皮书》是对《为黛西小姐开车》的复刻,只是对一对主角的性别和身份做了投机取巧的“微调”。《绿皮书》原本有可能对黑人钢琴家的身份困境展开更具穿透力的戏剧,比如他在赶路途中偶然看到了田地里贫穷、疲惫的黑人农民,那个场面的刺痛感是尖锐的,一个奋力离开自身阶层的人,既丧失了旧的归属,又没有获得新的认同,宛如一个体面的孤魂野鬼。但《绿皮书》没有胆量、更没有能力正面强攻马尔科姆遗留的议题,它息事宁人地炖出一碗“各自珍重,各自安好”的心灵鸡汤。
《纽约客》主笔布罗迪毫不客气地刻薄道:“《为黛西小姐开车》都过去29年了,《绿皮书》仍然能让奥斯卡评委们兴奋,这是行业的耻辱,我有理由怀疑,如今把票投给《绿皮书》的人们,就是当年抬举《为黛西小姐开车》的那些人。”(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