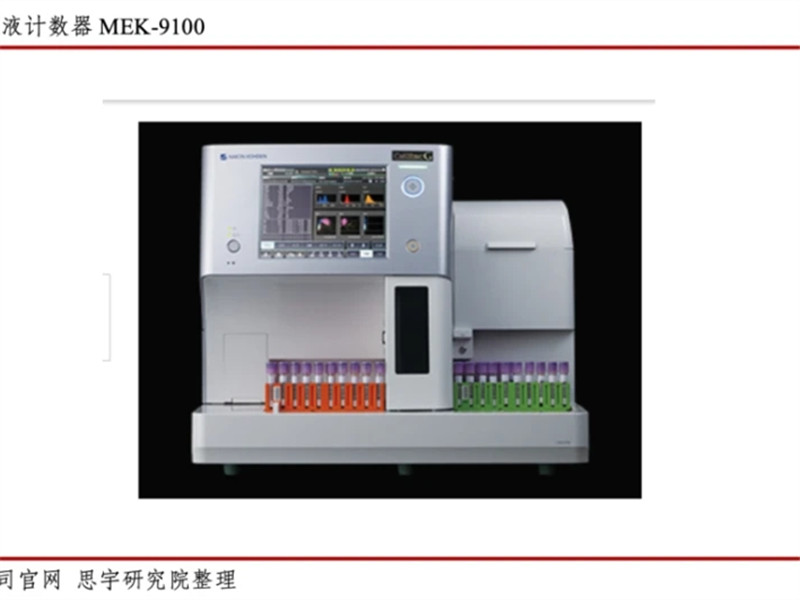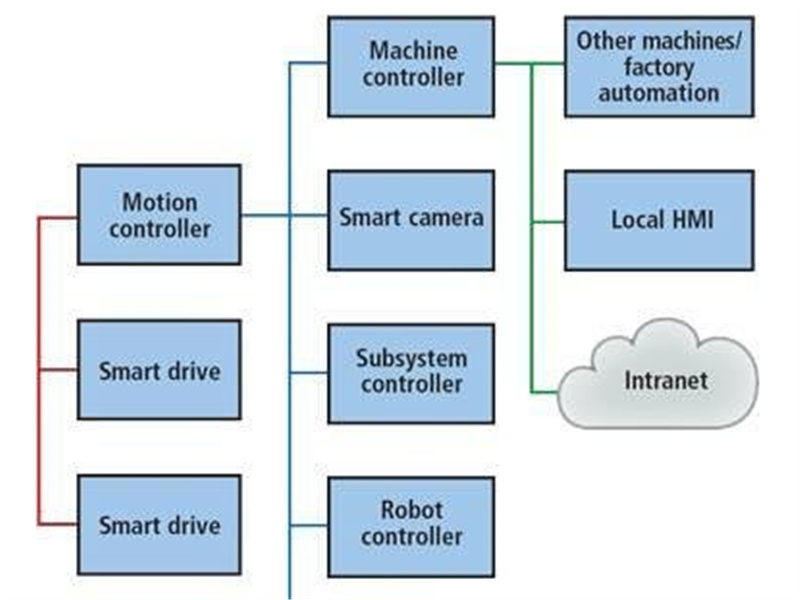经过半年多的酝酿,2019年2月5日,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2030》(Nationale Industriestrategie 2030)。
这份尚待证实批准的战略草案的副标题为“德国和欧洲工业政策的战略纲领”。其前言部分明确,制订该战略的目的在于应对“当今世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即“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创新进程极大加快、其他国家扩张性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如何长久地维持及发展德国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高度繁荣”。德国选择“有效地管理和引导新的全球挑战与发展”,具体路径是“更大程度地推进创新型技术并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其正文部分则肯定,以“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和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前瞻性、辅佐性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从中国的角度看来,这一战略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宣布,显得尤其意味深长。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言行无所不用其极地批判和反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国际大背景下,德国作为发达经济体却宣布取法中国——这是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第一时间的评论——并采取逻辑类似的产业政策路线,这让本已近乎强词夺理的美国情何以堪?又让素来宣称奉行多边主义、自由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Soziale Marktwirtschaft)的德国情何以堪?中国的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界应该如何看待德国的这份战略?
一、《国家工业战略2030》说了什么
该战略对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优劣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德国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成就斐然,德国在相当数量的“关键工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作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突破性创新和创新速度竞争中,德国有掉队的危险,因为竞争对手多采取了成功的工业战略/产业政策。
所以,德国必须制定产业政策,“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德国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因为德国的繁荣不仅仅事关德国的“生活方式”,更事关“德国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该战略提出,德国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包括:德国经济必须具有工业和技术的自主权与能力;工业占附加值总额(Gross Value Added)的比例应从目前的23%上升到2030年的25%;保持闭环的工业增值链;支持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做大;国家禁止外国企业并购德国企业虽然需要设限,但是国家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出面充当企业股份的购买者。其中,德国必争的关键技术领域、需要保护和扶植的重点企业名称一一列举。
二、德国政府为什么要出台这份战略
值得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是,阿尔特迈尔主导制订的这份战略将国家作为经济行为体的能动性和主导作用置于中心位置,因而其中所谓经济发展并不是首先指向全球意义上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而是指向“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框架下的民族国家或德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众多民族国家经济体在零和游戏意义上展开的“你死我活”的竞争。
就产业政策而论,德国“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是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就“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而言,德国的追赶对象是美国和中国的企业。至于战略中所谓德国产业政策的“欧洲维度”,则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政治正确修辞,并非重点所在。因此,德国舆论中不乏批评该战略是德国版“德国优先”的声音。
认识到这份战略的立足点是国家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才能对其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判断
。然而如果想在学理上逻辑自洽,这份战略必须回答以下貌似矛盾的问题,即德国历来标榜自己拥有“世界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为何却在经济形势空前向好之际——德国连年实现巨额财政盈余,贸易出超世界第一,失业率已降至统一以来的最低点——修正自己的发展观念,“突然发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发现,该战略文本对直接动因的表述殊为勉强。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世易时移”:“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却在日益增加,放弃多边协定的趋势也日益显现。”
但是,阿尔特迈尔所谓的这种“变革”,与此前德国经济在战后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相比,与德国近年主动倡导的“工业4.0”变革相比,甚至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的国际经贸关系相比,究竟已经质变、严峻到何种程度,以至于足以颠覆德国迄今为止的发展经验?比如其中提出要在德国留住“闭环的工业增值链”,这种明显背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做法与世界市场的变革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阿尔特迈尔表述的因果关系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或许德国的舆论界有足够犀利的眼神,因而能够不留情面地替阿尔特迈尔说出制订这份战略的隐含意图:
为了防御中国,或者说惧怕中国,或者说为了与中国展开竞争
。更大的可能是,在经济竞争中对中国处处设防早已属于德国舆论中“皇帝的新衣”,人人心知肚明。
阿尔特迈尔虽然在该战略文本中没有直接对中国提出指控,但是在产业政策部分对中国着墨最多;提到国家可以在外国企业对德国企业并购过程中发布禁令、甚至主动购买股份时,明显地指向近年来中国在德国的企业并购行为引发的德国舆论争议;建议修改德国和欧洲的竞争法以促进德国或欧洲公司的合并,甚至具体到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时,也都以中国的企业为假想敌。
如果把其中的涉华表述置于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德国从上一届联合政府时期即对中国企业在德国并购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KUKA)、半导体制造企业爱思强(Aixtron)、高压电网运营商50Herz等企业以及吉利打德国证券交易监管的擦边球入股戴姆勒等表达过不满、不安和杯葛;德国基民盟新任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去年9月即以执政党总书记的身份要求“必须要明确我们在哪些领域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中国投资者进入”;今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呼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等——不难看出,德国政界已经逐渐以对手的角度看待来自中国的竞争,甚至已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杯弓蛇影。
三、德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经过国际学界多年的研究和讨论,需不需要、存在不存在产业政策之类命题,在学理上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
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简单说来,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出现,主要是为了纠正市场机制的失灵,有效的产业政策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动态平衡。只要不是执迷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政府原教旨主义,就没有必要从经济哲学甚至道德的层面讨论“产业政策好还是市场好?”之类的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基金会(Ludwig Erhard Stiftung)将《国家工业战略2030》视为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背叛(“从没有任何一位经济部长如此明目张胆地背离社会市场经济的纲领”),这实际是把社会市场经济神圣化了,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路德维希艾哈德,生于1897 年,卒于1977年;1949至1966年间,先后担任德国经济部长和总理,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编注)
德国舆论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神圣化的另一面,是把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妖魔化
。路德维希艾哈德基金会称,“艾哈德的秩序政策与中国国家经济模式的产业政策是不可能和谐共处的”。事实上,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人应该知道,产业政策并非中国原创。美国政治学家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31—2010)的名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1982)在东亚和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神话一样,日本的产业政策曾经一度成为精英主义主导的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神话,中国只不过是施行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中最新的一个例子而已。
也许因为经济体量巨大和不同于西方的体制特点,中国给不具备经济学常识的某些德国人留下了“中国经济模式=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计划经济”的扭曲印象。而产业政策在德国也根本不是横空出世的新概念,《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有关产业政策的要点,实际上已经在2018年3月签订的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联合执政协议》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德国的替代性能源产业也完全是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因此,以所谓的中国产业政策为借口和出发点,论证或批判德国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如果不是虚伪,至少也是思维的短板。
既然“德国需不需要产业政策”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剩下的讨论就应该围绕着“德国需要什么产业政策”进行。但在这一方面,
《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论证给人留下了随意性、不全面性和前后矛盾的印象
。
例如,在提及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时,该战略认为“规模是关键”,企业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就难以与中美的对手展开竞争。所以德国有必要维护既有的龙头企业如西门子、蒂森克虏伯、汽车制造商、德意志银行、空中客车等企业。但以这些企业为例显然缺乏周全的考虑:蒂森克虏伯的传统欧洲钢铁业务已经于2018年与印度塔塔钢铁合并,双方在新成立的“蒂森克虏伯塔塔钢铁”中各占一半股份;德国汽车制造业对于德国政界的游说能力之强究竟是福是祸,在“柴油车排放门”丑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德国国家持股的空中客车日前不得不决定放弃生产A380大型客机,造成巨大的浪费,显然暴露了由国家补贴、受到政治决策影响的大型企业在经营理念上容易犯好大喜功的错误。
同样道理,《国家工业战略2030》呼吁国家直接介入极其重要的领域如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甚至直接资助电池的生产,同样存在国家越俎代庖取代企业经营主体的嫌疑。熟悉德国经济的人应该懂得,德国经济实力强大的秘诀并不在大型企业、龙头企业,而在大量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小型企业。该战略对企业规模的鼓吹,会不会扭曲市场竞争秩序,从而背离德国经济的创新源泉?这一系列的疑问,在战略文本中难以找到答案。
四、中国如何应对
通过以上分析,《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诸种问题逐渐显现:
与其说它是一份经过学界、工业界和政界充分沟通和讨论后得出的纲领性意见,不如说是德国政界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时的一种惊慌失措的自卫式反应;它没有选择“我的长处是什么”的主动思路,而更多选择了“如何不让对手发挥长处”的被动思路
。
中国的学界、经济界和政界当然首先关注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一旦成型后,对中国的企业尤其在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直接开展业务会产生何种影响,其次关心该战略在国际秩序中的宏观效应。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种角度展开思路:
首先,在商言商,市场经济还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至于德国政府企图通过《国家工业战略2030》扶植德国企业、提高外国企业在德国开展业务的门槛,只要在事先公告的法律等游戏规则之内,都是外国企业可以、也是必须接受的。我们相信,如果德国政府的行为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原则,德国以及欧洲社会自我监督的力量不会昏聩到指鹿为马的地步。比如在德国发布该战略的第二天,欧盟委员会就否决了德法两国铁路业巨头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并购交易,而推动和简化德国或欧洲企业的强强联手的程序、打造德国或欧洲的龙头企业本是阿尔特迈尔部长在战略中陈述的重点之一。
其次,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展开业务尤其是并购或介入所在国所谓的“关键技术领域”,还是较新的现象,中国的文化和体制在西方的认知中仍属于“陌生的他者”,“中国制造”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廉价品的印记。
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门槛,都需要中国的企业用遵守规则的经营以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一一克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本就没有捷径可走。对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实实在在涉及中国企业业务的部分,中国企业不妨看作是某种激励;其中捕风捉影的部分,则可以根据规则对应之,“清者自清”,完全无须自乱阵脚。
第三,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挑战既有国际贸易规则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德国试图采取“国家产业政策”确保德国的经济主权和安全,实际上也是从侧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和背书。各国民经济体之间光明正大的正当竞争本就无可厚非,我们无须进行价值评判,但是德国的道路选择无形中让美国对中国的攻击丧失了可信度。
第四,鉴于阿尔特迈尔部长宣称《国家工业战略2030》仅是相关讨论的“第一步”,还需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与工业部门、经济部门、工会组织和学术界的相关方”以及“联邦议院的各政党、各联邦州”进行深入讨论,以形成“含具体实施步骤的路线图”,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该战略一旦落实,必将具有一定的欧洲和国际维度,其对于现有国际贸易和经济秩序的冲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和具体分析。